1
唐宪宗元和年间,一位名叫吕岩(字洞宾)的儒生赴长安(今陕西西安市)应科举矜重,不中,在长安酒肆(今八仙宫)借酒浇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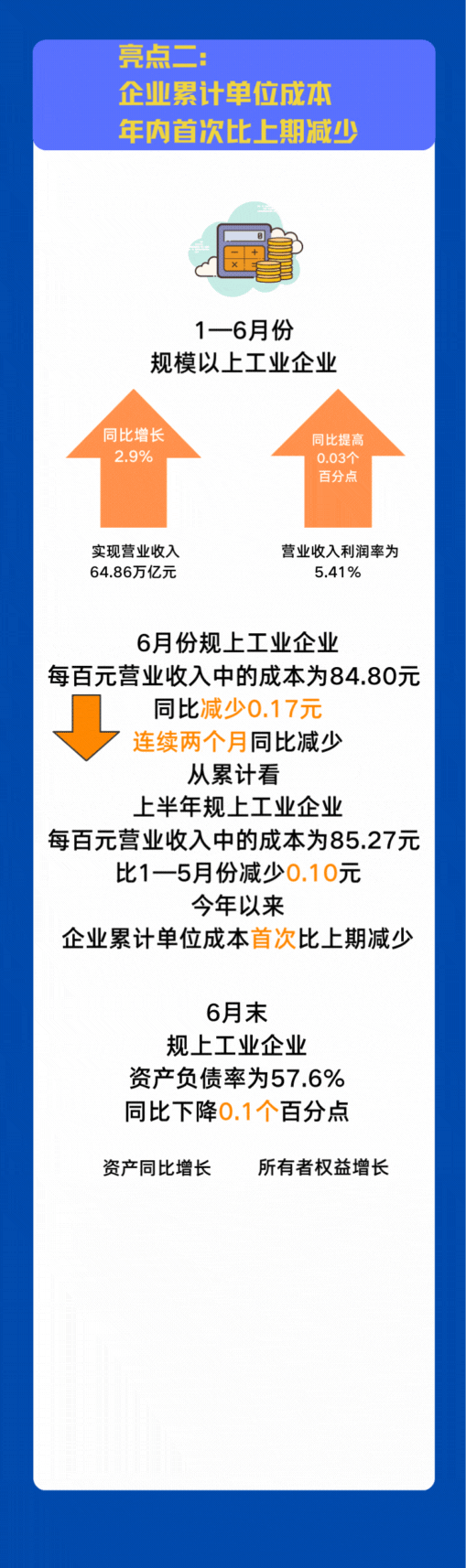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,有位仪容奇特的中年须眉也进了这家酒肆,他须髯很好意思,双眼又大又圆,孤苦羽士打扮,外穿鹤氅,头束总角,此东谈主姿色奕奕地来到吕岩眼前。
羽士向儒生作了个揖,就坐下来与他话语,劝吕岩修谈。
吕岩说:“等我考得大官公役,皎洁了祖先门风,然后再修谈不迟。”
羽士笑了笑,向他乞求吃一碗黄粱饭,吕岩就差东谈主为他作念饭。
吕岩忽然认为有些疲乏,那位羽士就从袖中拿出一个枕头来,递给他说:“这是‘如意枕’,淌若枕着这个枕头睡眠,就会获得你闲居想获得的东西。”儒生就接过枕头枕在头下睡去。
吕岩刚刚入睡,就看见有个使臣从外面进来,手捧天子圣旨宣召说:状元吕某接管天子的封诰,他的官运就这么启动了——他先是从方位州县官作念起,接着又莳植为朝廷要员,从此,台谏、翰苑秘阁以及多样清要官职都饱和作念过了,这中间或是被降职或是被莳植。

2
他前后共婚娶过两次,娶的都是荣华东谈主家女子,家中儿孙满堂,带冠簪的学仕和捏笏板的官员满门齐是。
就这么共资历了四十年的时辰,其后又独自擅权当了十年宰相,权势达到了顶峰,一天,忽然触犯龙颜,犯了重罪,被充公了通盘家产,驱散了爱妻、儿女和总共奴仆,把他充军到辽远地区。
这时,他孤身一东谈主,穷愁坎坷,体弱多病,又恰遇恶劣天气,风雪错杂,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气,忽然醒了,底本是一场大梦!
那位羽士见他醒来,就大笑着说:“黄粱饭还莫得煮熟,你却一梦就到了‘华胥国’!”
吕岩听后,吃惊地问:“你知谈我刚才作念的梦?”
羽士说:“你刚才的一场大梦,资历了各样世态和好多荣辱,几十年的时辰,不外一小会儿完毕。”
“你获得的东西也不值得为它容或,你失去的东西也无谓为它忧伤,并且你是有了大的觉醒之后才知谈这是一场大梦啊!东谈主活着间,一百年也不外是一场大梦长途呀!”
吕岩豁然觉醒说:“是啊,纵令是作念了最大的官,家中荣华得金玉满堂,依此梦来看,也只不外是造物主辱弄东谈主完毕,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呢!”
于是向羽士作礼再拜说:“先生不是凡东谈主吧?但愿您能带领教悔我这个愚昧东谈主。”
羽士说:“你既然仍是康健到了虚华的利与名其实仅仅东谈主生的镣铐,那么你悠扬念念想而追求通衢就容易多了!”
吕岩说:“我仅仅若干省悟一些,像《易经》中说的‘游魂为变’,死活之说,和‘尽性至命’的真谛等等,但愿师傅悯恤,告诉我修行和前途的措施。”

3
羽士千里默了转眼说:“百般表面协调协调,心里也就广袤彻底了;心无杂念都牢固下来,然后才智真性圆明,心理浮现则呼吸当然,人道是空而不空的‘玉虚’现象,又有什么‘游魂为变’之说?”
“真性纯一,就像天际那样寂靜明彻和寥廓,根底就不生也不朽,还有什么‘死生’的忧虑呢?东谈主到了这种田地,就会显然这么一个真谛:‘我本来是莫得生命的,又那儿来的死呢?’”
吕岩飘渺念念索了半天,终于彻底显然过来,于是再次拜谢说:“今生有幸,得遇仙师。刚才听了师傅的话,真实妙极了,混沌之间,真的能够‘我’的躯壳不存在了!”
羽士说:“我刚才对你讲的仅仅‘性尽’时的妙境中的一节长途,至于‘慧命’之法和临了的上等功夫,等你真的萧洒时再对你讲也不晚。”
吕岩谢意地问:“师傅尊姓大名?”
羽士答:“我复姓钟离星空app,单名叫权,‘云房’是我的字。我住在终南山,你日后不错来找我。”说完,飘然离去。
